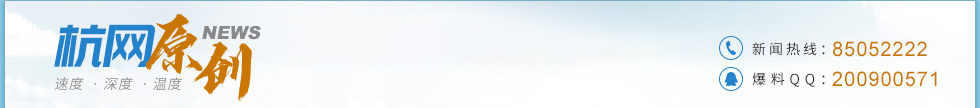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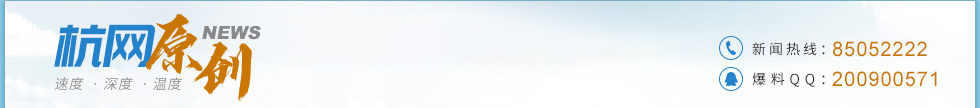
2019年9月18日下午,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公安分局岑港派出所所长林剑在处置一起某妇女放燃煤气自杀的警情中,为保护群众安全,不顾危险冲进中心现场,全身60%烧伤。
林剑被浙江省公安厅授予个人一等功,且入围央视新闻“2019十大暖新闻人物”评选活动。他的英勇事迹于12月13日晚在央视新闻频道播出。
为弘扬正能量,讴歌时代英雄,近日,浙江省公安厅宣传处开展“最美浙警之向危难逆行”采风活动,在浙江省公安作协主席艾璞的带领下,王海燕(宁波)、邵江红(绍兴)、邹文斌(嘉善)、毛华届(衢州)、支奕(舟山)、郑吉(舟山)、李建刚(杭州)等部分知名作家、诗人、摄影家赴定海采访。本网现陆续刊发作家诗人们写给海岛英雄的赞歌美文。


痛觉再现(小说)
文/洛华
我不知道那个女的为什么要向我道歉又道谢,我只觉得周身奇痒无比。
不是痒,是痛。也不是痛,是带着痛的痒。像……浑身像有一万只蚂蚁在咬,大概就是这种感受。
那个女的,身影越来越模糊,像是在摇晃,或者被风吹斜了。
我猛地惊醒。不不不,确切地说,是警校晨练集合的哨音把我唤醒。我利索地穿好警服,系好皮带,穿上警靴,扶直领带,戴正警帽。杭州冬天的清晨虽然有些冷,我还是没有穿所谓的棉毛衫,长袖内置衬衣的棉质恰到好处地贴合我的肌肤,从冰到暖的过程,那叫一个酸爽。室友说,喂,咱喝上一口同山烧再去集合吧,暖身!我说,来不及了。我一溜烟地跑出寝室。
同山烧?江南小茅台!酒啊!我们现在穿着警服不能喝酒吧?我一边跑一边意识到,我的醒来其实是进入了梦境,我梦见了我的少年。我疯狂地奔跑,渴望从梦境中醒来,身上的警服越箍越紧,越箍越紧。
我的意识在梦境里渐渐清醒。
那不是警服吧?是我身上的塑身衣,为了防止肌肉从尚未拼接好的肌肤缝隙里钻出来,长成一条又一条蚯蚓状的肉疙瘩,医生就给我穿了医用塑身衣。我的心脏跳得有些累,我的身上开始撕裂般疼痛,痛觉越来越明显。我真的后悔没有喝室友递来的同山烧,哪怕一口也好,入喉如泉水,如清冽的空气,会让我舒缓地从梦中醒来,要是不醒来呢,那如柴火般刚的酒味也一定能让我忘了周身的疼痛,就像关羽饮酒刮骨疗毒。
“人还在就好。”我听到我爹的声音。我知道我离现实更近一些了,可就是睁不开眼睛。
我感觉到手术刀生硬地从我的头顶剥下了一块皮,我像是被麻醉了,但每一刀,每一声“嗞”,都响在我的心上。
生了生了!我妈把我从床上摇醒,你老婆生了!
我醒来。我擦掉头上的虚汗,幸亏之前都是梦,原来是老婆生孩子,我才会做自己在手术台上的梦,昨晚加班太晚睡,睡沉得糊涂了。
刚想去医院,电话铃响了,临时要去单位。我只好对我妈说,妈,咱家喜事,备好同山烧,海半仙的!等我晚上回来一起庆祝。说完我就跑出了家门。
我越跑越不对劲。我怎么能连老婆怎么样、生男还是生女也没有问呢?这也太假了。可我即便知道自己在梦里,我还是醒不过来。我接警出警接警出警,像往常一样,面对形形色色的人,懦弱的,纠葛不清的,为非作歹的……我不停讲不停说不停喊。我数着。这一天,我出了三十几个警,好像把前半辈子的话都积攒到这一天里讲掉了。
我回到家里,老婆在教孩子写作业。我没有讲话,我径直走进厨房打开一瓶同山烧,咕咚咕咚地喝下去,爽!我再次经过老婆和孩子,走进卧室顾自躺下了。老婆追进来,说我不爱她和孩子。我还是没有讲话。我心里急切地想着,我怎么会不爱你们呢?可我还是没有讲话,我讲不出话来,我所有的话都在单位里、在接警出警处警的时候,讲光了。

我太累了,我很快就睡着了。
我梦见自己躺在病床上。不,这可能是真的。我听到我妈说,“还好这样的事情被我儿子碰到了,我儿子结过婚有了小孩,只要人还在,什么都不怕了。换成其他没结婚的小伙子,可怎么办哦,对象也找不出去了。”
我感觉自己流泪了。泪水顺着眼尾向枕边滑落,泪水爬过的肌肤,每一毫米每一纳米都在刺痛,我知道,是泪水咸咸地渗进了脸部尚未老陈的新皮里。
林剑,起来起来,出发了,督察去。
我醒来。午后的阳光透过落地玻璃窗,斜斜地照进来。

我原来叫林剑。我抬腕一看,快两点了,下午得下所去督察,我记得上午说好的,回头,还有个民警维权案件要办。
我整了整警服,戴上警帽和同事一起出发了。
天气真是闷热。空调间和室外完全两回事。警服很快就湿透了,浑身的热气像发不出去,汗好像都躲在警服里,它们也可能是躲在皮肤底下,只有少量的往外渗,哪怕是少量的,也已经湿了警服。然后,浑身刺痛。
怎么会刺痛呢?头,头顶也痛!辣,撕裂般地辣!
“麻药过了,病房里那瓶止痛药还接不上怎么办?”我听到一位护士在说。
我顾不上浑身的痛了,头顶的痛让我瞬间清醒。我意识到我正在进行第二次植皮手术,我的全身60%烧伤,医生只能揭我头顶的皮来养我身上的皮。麻药确实已经过了。我哭喊着向护士讨要纱布。我死死咬住那团纱布,忍受着接顶之痛。
我回想着自己,怎样一步一步走进医院。身上脸上表层的皮肉都熟了,我每迈一步,好像身上的皮肉都会挂不住似地颤抖,并且淌下油脂来,顺着脚脖子落到地面上,形成一个个特殊的脚印。我庆幸自己还活着,也庆幸那个女的还活着。只是这痛!要是能闷一口同山烧就好了。
止痛药,一滴一滴地落进我的血管里。所有的痛疼都有了一些缓释。
打火机“呲啪”的声音钻入我的耳朵。
整个世界都慢了下来。我看到火苗在她手上摇曳,像跳舞一样地左摇右摆。一声巨响,气浪向我袭来,像风如浪,生平从未体验过的烫,灼热,警服在瞬间熔化,紧紧贴在我的身上,我也听到我的每一根汗毛在燃烧,我的每一寸肌肤在燃烧,它们嗞嗞作响,周身在冒油以及绽裂,我痛得弓起身子,一边下意识地抓住她的手,我必须带她一起逃离现场,要是我就这样死了,死前连一口酒也没有喝,那怎么成!
实在说不清是我拽着她跑出来的,还是气浪把我推出来的时候我把她拖了出来,反正结果是我命硬,没死。她也得救了。
命硬也挡不住剧痛。
风吹在身上,就是走动或者身边有人走动,空气流动起来都让我觉得痛不欲生。我想像野兽一样嘶吼,来抵挡这无法形容的痛,嗓子早已被烟尘灌满,我的每一声“啊”都像破棉絮般断续无力。同事找到了我,他想扶我,无处下手,他给我喂水,我像大猩猩一样垂着无能支配的双臂,接受每一口水。他哭了,一个大男人他竟然当着另一个男人哭了。
“所长,小心喝,粥温温的应该刚好。”我醒来,单位的兄弟对我说,“第三次植皮手术也很成功。”
我想起来,那天我在开会,民警跟我汇报说有一个自杀警情,女的开了煤气要引爆自杀!我就近赶去警情现场,兄弟们也已经在出警路上。

一幢两层民房,隔壁,隔壁的隔壁,也是民房,都是民房。里边有多少煤气?不清楚。一旦引爆,扬言自杀者自己的性命不说,万一火势大还可能殃及邻居们。千钧一发。这应该是我从警十七年来,最称得上千钧一发的时候。
民房的门紧闭着,门后的危险我不是不知道。也许我可以拖到兄弟们都到了,再指挥他们进去解救。可是,他们每一个都比我年轻。冲吧,争取时间,就算我耗得起,我身上的这身警服也耗不起。
我破门而入。
“要是现在能来碗同山烧多好。”我喝下一口粥,对兄弟说,“医生不让啊!”
“所长,那你就赶紧恢复!”
一个女的摇摇晃晃走到我的病房门口,向我道歉又道谢。这回我看清楚了,我朝她笑笑。
兄弟说,“所长,她害己又害人,你看你,还要把先到救护车让给她,幸好医生让你也一起上车了,一路蹲来难是难了点,好在没错过最佳治疗时间。”
我觉得周身奇痒无比,兄弟刚好拿起来棉锤帮我敲起来。
“都过去了。”我说。
作者简介
洛华,姓名郑吉,系浙江省作协会员,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作品散见《小小说选刊》、《百花园》、《安徽文学》、《浙江作家》、《海山文艺》、《舟山警苑》等刊及中国公安文学精选网等网刊。
相关链接:
浙江作家诗人摄影家给一位海岛英雄画像之一 诗歌——致战友林剑
浙江作家诗人给一位海岛英雄画像之二 有一种疼叫林剑的不悔选择

